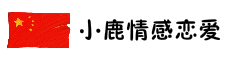《庄子》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有一男子叫尾生,与一女子相约会于某桥下。女子未至,水来,尾生不肯离开,被洪水吞噬,抱桥梁而死。
动物中也可见爱情。
元好问赴京考试,路遇一打猎者,打猎者说,早上捕获一对大雁,杀大雁时,一只逃出,但在空中哀鸣盘旋,久久不能去,后见伴侣死,竟从空中疾飞而下,以头击地而死。
元好问听了很感动,买下两只大雁埋葬,写下千古动人的词作《雁丘词》,其中道: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动物固然亦有爱情,但仍不得不承认,人类之爱情要复杂,狂热得多。
人类之爱情,究竟是如何起源的呢?
远古时,我们祖先刚刚脱离树上,生活于原野。
与动物相比,我们没有尖利的牙齿,锐利的爪子,自身之安全受到强烈威胁。
不过幸好我们学会直立行走,直立行走时视角高于一般爬行动物,获得更广阔的视野,令我们能更早发现视线范围内的攻击危险;另一方面,高远的视野会接受更多信息,刺激大脑,促使脑神经链接更复杂,具备了初步的想象能力。
想象力很重要,动物进入发情期,向异性求偶,更多是由于本能。人类有了想象力后,对于异性除了本能,会产生各种幻想,如将对方的身形,举动,声音等,都与本能联系起来,产生甜蜜,愉悦的感觉。
如此一来,爱便植根于欲望,又超脱了欲望。
直立带来的想象能力,也令我们深刻认识到工具的重要性。
我们的近亲大猩猩在游戏时,往往喜欢从树上冲下,挥舞树枝,证明自己的力量,周围大猩猩会以兴奋的嚎叫予以鼓励,但是大猩猩用木棍能做的事很有限。
人类祖先也很早使用木棍,但是比动物更复杂思维让我们感知到,木棍是身体的延伸,可以更好攻击其他动物。由于联想能力,人类使用木棍日趋娴熟后,进而拓展到学会使用其他粗糙工具。
令人类生活乃至思维进一步发生巨大变化的工具是火。火最早取于因雷电燃烧的森林,或太阳直射下枯木的自燃。
人们学会保存火种,用火后,开始驱赶一些岩洞中的野兽,成为容身之所。
洞穴内更温暖安全,于洞口燃烧一团火,不仅能驱赶野兽,还能带来光明,大大增加我们活动时间。
生活在野外,需要的不是今日之书本知识,乃是实际生活经验,如怎样的地方容易有猛兽出没,何种野果有毒。
年长者由于人生历程更长,其意见很重要。
夜晚,人们围坐于火堆前,枯索无聊,会听老人们们讲述各种生活经验,自然也会讲到老人们的幼年故事。
最早讲故事的人便诞生于这一时期。老人们讲述过去经历时,不可避免会有人虚构,加剧故事情节冲突,以勾起听众趣味。
人们也因此尊崇老人。老人具有大量生存经验,是智慧的象征,也是历史与文化的传递者,
在原始先民“北京人”的遗址,考古学者们发现,许多头骨被穿孔。人们推测,这是因为老人是智慧象征,早期先民们会在人死后,食用其脑,认为可以增进自身智慧。
故事会进一步刺激人的大脑发育,拓展人们的想象能力。
早期女性在群体分工中,负责储存,看管食物,更多时间生活在洞穴中,人们将女性与家,温暖联系在一起。
男性负责狩猎,进攻,会令人将其与安全感,力量,责任联系在一起。
想象能力的日趋复杂,进一步令人类的爱情变得与动物间的依恋情感有了更截然分别。
于是我们今天能看到无数单身青年,宁可骄傲单身,也不愿简单屈从于最纯粹原始的欲望,社会压力。
于是我们看到有人相爱结婚,又因为没有了爱,鼓起勇气,面对强大世俗压力离婚。
杜拉斯说,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疲惫生活里的英雄梦想。
爱是我们先民从残酷进化历程中一点点脱离野蛮,蒙昧,雕琢而来。是人类文化中的最高价值之一,也是每个人在有涯之生,残酷荒原中,心中不灭的希望和星光。
我的面相课“面相与天命”,开课啦!
这门课程将以生动,专业、图文并茂的形式,讲述面相学专业基础知识,个性与天命之间关系,每三天更新一次,从加入之日起,为期三个月。
它将成为你职场面相识人,与他人打开话题,深入认识自我,探究传统文化的绝佳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