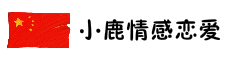说到中秋,天空中的那轮明月,一定是绕不开的话题。
崇拜月亮,是“古今中外”所有文化的普遍现象;这源于人类文化信仰中,原始的天体崇拜。作为漫漫长夜中,最明亮的天体;月亮的圆缺变化,与人体生理现象的奇妙联系,以及月球表面上的那些不规则的马赛克(暗斑)等,都为它增添了数层神秘面纱,引发人们无尽的幻想。
01 生殖之神
在中国早期的原始神话中,月亮是一只肚腹浑圆,且可膨大缩小的神蛙(蟾蜍)。这与月亮的圆缺,和女性的生理现象有关。
古人发现,月亮由圆到缺,28天是一个变化周期;又发现女性的生理周期(月经)也是28天,于是笃信“天人感应”的古代中国人,便将这一生理现象与月亮联系起来,称之为“月经”。
后来人们又从生活中观察总结到:女性有了月经,才能怀孕生育;怀孕后,月经终止,分娩后月经恢复;女人闭经后,即失去生育能力。于是朴素的认为:“人是由经血生成”。
因此,古人们为了多生育,男女同房会特别注重女性的生理周期,认为月经到来时是最好的生育时机。清代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林氏》一文就有“每值落红,辄一为之(交媾)后,生二男一女”的说法(这是古人在不了解人类生育原理时期的朴素认知;关于“性与生育健康”的问题,最好翻阅正规卫生医疗机构认证的出版物,或咨询专科医生)。

女性先民们看到自己怀胎后日渐鼓起,分娩后又重新平复的肚子。又看到同样能够变化肚子的蟾蜍,便朴素的将蟾蜍与生殖联系起来,将蟾蜍认作女性生殖崇拜的象征物。
而同样可以变化“肚皮”大小的月亮,也被人们联系起来。认为月亮是蟾蜍神的化身,掌握着生殖的神力。
比如《汉书》中记载,汉元帝皇后,元后的母亲李氏,梦月入其怀而生元后。三国时期的吴侯孙策出生前,也有传说称“其母梦月入怀而生之”。这种“感应生殖”的传说,在古代各民族中有很多。
大约成书于三国时期的《周公解梦》中,就有梦“日月会合妻有子”,“吞日月当生贵子”,“月入怀主生贵女”等占梦口诀。
可见“月神掌管生育”的影响十分深远。
02 爱恋之神
月神既然已经掌管了生育,自然就很容易与“性爱”联系上。
成书于春秋时代的《诗经》中,就有“热恋中的情人,在明月下盟誓定情,拜祷月神”的记载。
男女谈情说爱,常在“花前月下”,除了因为花与月,在我们的文化中都有浪漫的意味;还因为传说中的月神,是一个温柔慈悲的女神。情人们喜欢在她面前赌誓,或请她来监察评理。
在我看来,因为月亮女神温柔慈悲,就找她来评理见证,就是在欺负老实人。欺负善良的女神,不好意思天打雷劈,直接弄死那些食言乱语,爱说鬼话的渣男渣女们,哈哈。

有趣的是,我国许多少数民族的拜月活动,也都与爱恋有关。
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苗族的“跳月”——每逢中秋之夜,明月光照遍山寨,苗家儿女纷纷来到林间的空地上,载歌载舞,举行“跳月”仪式。青年男女在“跳月”中,寻找自己心上人,倾吐爱慕之情,以期待结下“百年之好”——功能上,与西方贵族的联谊舞会大同小异,主题都是爱恋。
03 团圆之神
恋人们崇拜月亮,还因为她是团圆之神。很多失散的恋人,也会拜求月神,祈求他们爱情的见证者,能够帮助他们团圆。还真是“一事不劳二主”啊。
元代杂剧大家关汉卿,写过一出《闺怨佳人拜月亭》。剧中尚书之女王瑞兰与书生蒋世隆在兵乱中邂逅相遇,二人在患难中产生爱情,并私定终身,结为夫妻。后王蒋二人被王尚书强行拆散。夜间,瑞兰在庭院中拜月,祈求月神保佑自己能与丈夫蒋世隆重新团聚:“愿天下心厮爱的夫妇,永无分离”。
《西厢记》里的崔莺莺,也虔诚的对月神倾诉“希望遇上意中人”的衷肠。
在清初丁耀亢所著《续金瓶梅》中的第二十八回,一对痴男怨女郑五卿和银瓶,在私尝禁果后,便双双对月神赌誓永不变心——玉卿,银瓶推开楼窗,双双跪倒道:“我两人有一人负心的,就死于千刀万剑之下。”
这些都是当时世俗恋情生活的真实写照。

当宋代大文人苏轼曾写下“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千古绝唱后,更将祈求恋人团聚的心情,延伸到祈求家人们阖家团圆的诉求上,完成了一次重要升华。(请不要在意这里的时空顺序,观点的重要性,在于它什么时候受到大众的认同,而不在于它的提出时间。)
古人在两地分隔的时候,不要说相聚了,连通信都很难。但思念总是需要找一个媒介的,而月亮就担当了这个角色。因为在同一个时间,无论两个人隔着多远,看到的都是同一轮明月。
望月怀远,思念亲友不一定非要在八月十五,任何时候都可以。但是因为苏轼的这首词,让八月十五的月亮有了特殊的意义。
苏轼借助一个“圆”字,一指代月亮的圆形,二是人生的圆满,三是亲人的团圆,三重意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秋的月圆和人间的团圆,人间的团圆和人生的圆满,就这样交织在一起。
当观念上,大家认同月亮能够代表人世间悲欢离合,能够引导家家户户的亲人们团聚到一起,“吃团圆月饼,吃团圆饭,喝团圆酒,拜月赏月”的时候,月神就是我们心中的团圆之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