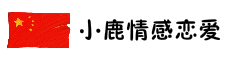人世间有一种动容的爱情,叫三毛与荷西
撒哈拉的风沙里,吹的是你我的故事
Echo,你等我六年,我有四年大学要念,还有两年兵役要服,六年一过,我就娶你。
我们都还年轻,你也才高三,怎么就想结婚了呢?
我是碰到你之后才想结婚的
我是极不愿意再婚后失去独立的人格和内心的自由自在的,婚后我还是“我行我素”,要不然不结婚。
我就要你“你行你素”,失去你的个性作风,我何必娶你!
三毛找到了那个愿意放弃自己的人生梦想,爱她的潇洒、理解她的疯狂、成全她的自由,只为与她相伴一生的人。
三毛是一匹脱缰奔跑的野马,而荷西愿意毫无保留给她一片无边无际的草原。
-"你想嫁怎样的人?"
-"看顺眼的,千万富翁也嫁;看不顺眼的,亿万富翁也嫁。"
-"就是想嫁个有钱的。"
-"也有例外。"
-"要是嫁给我呢?"
-"要是你的话,只要有够吃饭的的钱。"
-"那你吃得多吗?"
-"不多不多,以后还可以少吃点。"
三毛说荷西是她的一生挚爱。
三毛与荷西的结合,是彼此都希望与对方结伴而行的结果,三毛是个独立的女人,如她自己所言,“双方对彼此都没有过分的要求和占领”
荷西也成全了三毛
这个逍遥在沙漠中中的平凡的主妇,也是多产的作家、聪慧的艺术家,和她的大胡子先生,即便粗衣陋食,仍然幸福快乐。
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切就是最好的安排。
两条垂落的麻花辫,一身吉卜赛长裙,喋喋不休地说着。
一把蓬松的大胡子,一件脱色的衬衫,傻傻地望着她笑。

*三毛与荷西
撒哈拉沙漠的天际边,是三毛与荷西,并肩漫步在夕阳里
踏尽红尘何处是吾乡,是那梦中的橄榄树
结婚的第六年,荷西走了。
那个皓月当空的夜晚,日尽潮去
“于是不愿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
那一刻,半个三毛已经跟着离开了。
撒哈拉的每一粒沙都是想念,流浪从此失去意义。
“走得突然,我们来不及告别。这样也好,因为我们永远不告别“
到底是不愿告别的。
“荷西这个男人世上无双,我至死爱他,爱他,爱他,死也不能叫我与他分离。经沧海,除却巫山,他的死,成全了我们永生的爱情,亲情,赞赏。我哭他,是我不够豁达,人生不过白驹过隙,就算与他活一百年,也是个死,五十步笑百步。但我情愿上刀山,下油锅,如果我可以再与他生活一年、一天、一小时。我贪心......”
三毛和荷西约定下辈子各自要过不一样的人生不会在一起,所以这辈子要好好珍惜。
而老天不愿予这一世一个圆满,或许是早已为他们许下了再一世、生生世世的因缘

*抽烟的三毛
12年后,整一个三毛终也彻底远逝
花落人亡
离人梦里花落几分,也不得而知了
她继续流浪,
也许独行天涯,也许共赴海角
她终究是自由了
梦里的花又开了,花开成海
三毛一生有三段刻个铭心的爱情,两次要为了追随爱人结束自己。但她从来都是自己生命的主宰。
勇敢去表达爱,不强求被爱,拥抱自己的人生,为自己而活是她一生的坚守。
1908年1月9日出生在巴黎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和法国哲学家萨特演绎了一段对世界和时代而言都意义深远的开放式恋情。
在前段时间热播的美剧《致命女人》中,由刘玉玲扮演的那个性格火爆古怪、吸引“小奶狗”的女人,也叫Simone。
不管这是否有意为之,我们都应该记住这位女性的名字,她的人生是一场为了
而奋斗的传奇,而她的爱情也是如此。
萨特出生于1905年6月21日,比波伏娃大两岁半,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波伏娃则在索邦大学就读。
当时,萨特那个和他最好的朋友保尔·尼赞,组成了一个反传统者和煽动者的小团体,他们会坐在咖啡馆里打发时光,对着任何冒险靠近他们的人,大声抨击哲学、文学和中产阶级行为中不可冒犯的观念。
他们曾因为拒绝参加学校的宗教知识考试而激起了众怒,因为谈论人是肉体欲望的集合,而不是高贵的灵魂,震惊了所有人。
正是这个时候,波伏娃通过一位名叫马休的朋友,接触到了萨特的团体。她觉得他们既令人兴奋,也让人生畏。
她因为对待学业非常认真而遭到了他们的嘲笑——可她当然要认真对待了,因为她想要的一切都需要努力争取。教育对她意味着自由和自主,而男生们却把这些视为理所当然。
不过,这个团体接纳了她,她和萨特也成了朋友。
他和其他人称她为Castor或者the Beaver,大概是指她总是一副忙忙碌碌的样子,但同时也是她的姓氏和相近英文单词的一个双关语。
萨特逐渐把波伏娃当成了他的盟友,他最中意的对话者,他任何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和最佳读者。他们会阅读彼此的著作,并且几乎每天都会讨论他们的思想。
他们是彼此的“会饮哲学家”,可以谈论一切对话。
他们考虑过结婚,但两人都不想要一场中产阶级的婚姻——或者孩子。波伏娃和她的母亲有很深的矛盾,这使得她对家庭关系有着强烈的不信任。

*萨特与波伏娃
萨特和波伏娃之间惊世骇俗的关系,开始于某个傍晚。
两人坐在杜乐丽宫花园的石凳上,达成了一项协议:接下来两年,他们尝试当情侣,之后再决定是否续约、分手,或以某种方式改变他们的关系。
波伏娃在她的回忆录里坦言道,自己一开始被这种临时约定吓到了。她对这次交谈的叙述,充满了被强烈情感铭刻于心的细节:
那里有一种用作靠背的栏杆,离墙壁稍稍有些距离;在后面那个像笼子一样的空间里,有一只猫在喵喵叫。这个可怜的家伙太大,卡住了;可它是怎么进去的啊?有个女人过来喂了这只猫一些肉。然后,萨特说:“我们来签一份两年的合约吧。”
他们平安度过了那两年时光,然后成了一段长期但不排他的情感关系中的搭档,从1929年一直持续到1980年萨特去世。

*波伏娃
在五十年的时间里,这段关系由自由和友谊两个原则定义而成。
有一个关于他们俩的经典笑话很早就得到了流传:
两人在参观动物园时,看到一头样子惨兮兮的胖海象,它叹了口气,一边抬眼看着天空,一边让饲养员把鱼塞进它嘴里,就仿佛在恳求一样。
从那以后,萨特每次闷闷不乐时,波伏娃都会提醒他想想那只海象。他就翻翻白眼,滑稽地叹息一声,他们俩都会感觉好些。
他们之间有一种外人难以撼动的默契。其中最重要的元素在于:
他们的关系是一种作家间的关系。
萨特和波伏娃都无法控制自己的交流欲望。他们写日记写信,告诉彼此每天的每一个细节。
在20世纪的50年间,他们之间流转的书面和口头文字的数量,就连想想都会令人不知所措。
萨特总是第一个阅读波伏娃著作的人,他的批评深得她的信任,而他也会督促她写更多。
要是逮到她稍有惰怠,他就会斥责她:“但是,Caster,你为什么要停止思考,你为什么不工作?我以为你是想写作的呀?你不想变成一个家庭主妇吧,你想吗?”
情绪的起伏来了又走,工作一如往常。工作!在咖啡馆工作,旅行时工作,在家工作。任何时候,当他们在同一个城市时,他们就会一起工作,无论生活里有什么其他事情发生。
在一部1967年为加拿大电视台摄制的纪录片里,你可以看到,他们大口地 抽着香烟,除了钢笔疾书的声音外,非常安静。
波伏娃在一本练习本上写作,萨特在审阅一页手稿,这就像某种不断循环播放的纪念影像。
柯莱特 ·奥德里对此总结道: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关系,我以前从来都没见过。我无法描述和这两人在一起时的样子。他们的关系太热烈了,以至于有时候会让目睹这种关系的人很遗憾自己不能拥有。”
属于萨特和波伏娃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他们之间的爱情,总会带着某种神秘的诱惑力,它意味着
延伸,包容和理解;
这种爱情不是自私的,它从不占有,只是交流;就像两棵彼此靠近的树,根在地下交错,却伸展枝干拥抱属于自己的阳光。
波伏娃的爱情不只属于萨特,而属于整个世界,正是因为将整个生命投入对同时代的命运中,这种开放式才显得伟大而庄重。
波伏娃用自己的思想与行动,呈现出女性改变世界的力量。
林徽因秀外慧中、多才多艺。
曾旅英留美,深得东西方艺术之真谛,兼具中西之美,既秉有大家闺秀的风度,又具备中国传统女性所缺乏的独立精神和现代气质。
林徽因终其一生,经历了三段感情。
徐志摩版《爱在黎明破晓前》,浪漫诗人对她痴狂,并开中国现代离婚之先河;
林徽因对于徐志摩的热情,有着不可信任的直觉,徐志摩的浪漫与飘逸是她所欣赏的,但也是她无法把握的,以至于自己无法焕发出同样的激情去应和。
林徽因对于徐志摩的“你是我波心一点光”的爱最终遗弃,究竟是因为她的明智:
林徽因曾对自己的儿女说:“徐志摩当初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而事实上我并不是那样的人。”
她的理性使她能够游刃有余地把握着距离的分寸,让自己永远存活成诗人心中的白月光。
林徽因的朋友费慰梅女士曾说过:
“我觉得徽音和志摩的关系,非情爱而是浪漫,更多的还是文学关系。在我的印象里,徽音是被徐志摩的性格、热忱和他对自己的狂恋所迷惑,然而她只有十六岁,并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世故。”
的确,徐志摩满脑子想苦苦求而不得的的其实是他理想中的英国才女,那是他对理想爱情的一种现实映射。
那种镜花水月的爱情,固然是一种可贵的浪漫情怀,但终究少了理智的自制及对他人的体恤,亦使他本人深受其害。
梁思成版《爱在日落黄昏时》,建筑学家丈夫视她为不可或缺的事业伴侣和灵感的源泉。

*梁思成与林徽因
婚前,梁思成问林徽因:“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
林徽因答:
“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听我了吗?”
婚后,梁思成曾诙谐地对朋友说:
“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是,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
金岳霖版《爱在午夜降临前》,她犹豫不决之时,金岳霖大度退出。
金因她不婚,倾尽大半生时光“逐林而居”,将单恋与怀念持续终生。
她是才女作家,是一代佳人。
流逝的时光之水也冲洗不掉她的传世风华,反而更加迷人,令人追寻。

*林徽因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风花雪月固然浪漫,但是更多的或许是后人的添油加醋、加工渲染,期待迎合受众。
她是一个诗人,一个经历传奇的女子,但是她远远不仅是这些。
兵荒马乱的年代里,不顾旧病在身,用自己的一腔执着对文化古迹大幅修补抢救的是她;
为了保护北京古建筑,怒斥北京副市长吴晗的,亦是她;
参与国徽设计、改造北京传统工艺品景泰蓝、参加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历史上第一个敢于踏上皇帝祭天宫殿屋顶等等等等,都是她。
这才是她的独特之处,永远无法被复制的绝代风华。
坚贞、刚毅、温柔、贤良并不矛盾得重合在她的身上,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刚柔并济。
她的周身沾染着江南的温柔和诗意,一如人间四月般美好。
在1929年的西贡,明晃晃的阳光让人睁不开眼睛。
湄公河的粼粼波光投射在一位纤细的,脸上带着奇异的欲望的少女深邃的眼眶,她倚靠在轮船的栏杆上,极目远眺,试图在熙攘嘈杂的人群当中,寻找一抹身影,以浇灭灼烧着的欲望和日复一日的期待。
终于她发现,在难以逾越的人群背后,有辆车一直安静地停在那里。
她伸展修长的脖颈,越过重重障碍,同车里那个深沉而浪漫的男人对视。

*电影《情人》
这是1992年在法国上映的电影《情人》中的经典片段,也是杜拉斯本人的真实经历。
15岁的杜拉斯在西贡的旅途当中遇到了李云泰,她的中国情人,她一生当中最为深刻的爱恋。
在湄公河堤岸的公寓里,铺天盖地的欲望将她吞噬,她沉沦其中,带一种少女的甜蜜,也带一种肆意妄为的绝望。
“从那时起,我的性经验总是十分丰富的,甚至是粗暴的。”这位富有的中国情人满足她的物欲,也填满她的身体,这是杜拉斯的第一段真正意义上的爱情 。
其实,早在15岁之前,杜拉斯就已经经受过情欲的洗礼。
她在《中国北方的情人》中袒露,在遇见李云泰之前,她和她的二哥保尔曾有一段畸形又温暖的感情。
面对凶暴的大哥与偏心的母亲,兄妹二人相依相偎,从对方那里完成了情欲的启蒙,这样惊世骇俗的际遇正如杜拉斯儿时房间正对的那片热带雨林,潮湿、隐秘、充满野性。
“你对李云泰还留有什么其他的记忆?”一位记者曾经问杜拉斯。
“欲望的力量,彻彻底底,超越感情,不具人性,盲目。没办法形容。我爱这个男人对我的爱,还有那情欲,每次都被我们俩天差地远的歧义所燃烧。”
这段溽热、奔放的爱情持续了两年,就被永远地留在了西贡。之后杜拉斯离开了西贡,回到了巴黎。
“15岁那年,杜拉斯遇见了一个中国男人李云泰,他成为她的第一个也是终身难忘的情人。
1939年,与她结婚的罗贝尔·昂泰尔姆是她前一个情人的好朋友,也是她一生信赖的弟弟和朋友。
1942年,她认识了迪奥尼·马斯科洛,双方坠入爱河。
此后,她又经历了一段感情。
直到70岁时,她认识了不到27岁的大学生杨·安德烈亚,他成为了她的最后一个情人,一直陪她走完了82岁人生。”
百度词条上对杜拉斯的情史极为简练,并不足以展现出杜拉斯徘徊在爱与欲望之中的纠结,以及她无数次在作品当中提到的,宿命般的孤独与别离。
杜拉斯作为名作家,自然有不少追随者,每天都会有很多陌生人写信过来,与杜拉斯探讨文学与创作,或是表达自己的敬佩之情。
而其中,有一个叫扬·安德烈亚的年轻人,连续给杜拉斯写了2年的信。
这2年的通信开启了杜拉斯新的,同时也是最后一段奇异的恋情。

*扬与杜拉斯
在66岁时,杜拉斯与27岁的同性恋者扬同居了。
39岁的年龄差距和扬同性恋的身份让他与杜拉斯的结合甚至带有一种神圣的意味,超越世俗的禁锢与情欲的诱惑,他们靠两颗诚挚灵魂所产生的共鸣来相爱。
杜拉斯说:
“跟扬在一起,我再度发现:一个人一生中所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就是无法去爱。”
1996年3月3日,杜拉斯在扬的陪伴下去世了。
墓碑上只有简单的两个字母——她的名字缩写M.D,没有墓志铭,就像她的很多作品一样,她的一生,永远没有结局。
她永远怀着一种英雄梦想,在隐秘的爱与情欲之间野蛮地生长,倨傲地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