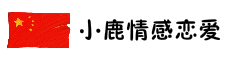“这是一只活脱从狄更斯书里蹦出来的可爱兔子,如果让你见到了,不爱死才怪,一走进店内,声嚣全被关门外,一阵古书的陈旧气味扑面而来,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是一种混杂着霉味、常年积沉的气息加上墙壁、地板散发的木头香......店内左手边有张书桌,坐着一位年约五十、长着一只荷加斯式鼻子的男士。”。
——《查令十字街84号》
以上这段话是出自作家Helene Hanff的书信集小说《查令十字街84号》中的一封信中的内容。Helene Hanff的朋友Maxine Stuart在1951年9月10日写于伦敦某演出剧场的后台,信中Maxine向海莲详细描述了这家——马克斯与科恩书店的样子。此时,距离Helene·hanff第一次写信于该书店已经两年时间。海莲9月15日在给友人Maxine的回信中写道:“真多亏了你的慧心巧手,书店简直被你给写活了——你的文笔实在比我好得太多啦!......我不想让你以为我是酸葡萄,不过我实在不明白,你究竟是何德何能?老天竟任由你饱览遍逛“我的书店”;而我为什么就只得乖乖蹲在九十五大街的破公寓里,埋头写着这劳什子《埃勒里·奎因的冒险》电视剧集脚本!”
可能此时的Helene Hanff不会想到,在接下来的18年中,她与这家书店的人生交集以及她最后踏上去往伦敦来到这家书店的时间是如此漫长......而一切,开始于一封很简单的从纽约到伦敦的商业性的信函。
1949年十月,伦敦市中心中西二区查令十字街84号上的一家古书书店——马克斯与科恩书店的经理Frankie Doel收到来自纽约的一封信:
先生:
你们在《星期六文学评论》的广告上说你们长于经营绝版的书籍,你们所用的“珍本书商”一词让我有些害怕,因为我总是把“珍本”与昂贵相联的。我是位穷作家,但对书却有一些“珍本”般的嗜好,我所要的书在这里都很难买到……寄上我最急需的书的名单,如果你们有干干净净不超过五美元一本的二手货,请将此函视作订购单,给我悉数寄来。
一九四九年十月五日
Helene Hanff
海莲还特意在信的结尾特地注明了“小姐”,其实, 这位写信的小姐是一位叫Helene Hanff的穷作家,此年已三十有三,是一位以写电视、舞台剧本为生的自由撰稿人。Frankie在收到来信后,在没有提前收到定金、没有第三方支付平台、也没有确定大西洋包不包邮的情况下,挑选了两本品相相对不错的书直接寄与纽约。
当然,Helene Hanff是一个非常讲信用的女人,她在分不清美元与欧元的汇率的情况下,多寄了几张美元钞票,从此开启了自己与伦敦的这家马克思与科恩的书店长达二十年的书信往来。
其实有人在《查令十字街84号》中计算过,在长达二十年中的书信来往中,Helene Hanff一共所购书籍不超过40本。对于一个爱书的作家来说,这完全算不上多,但是,漫长的20年时光,海莲与书店员工的友谊跨越了大西洋。当时英国正处于二战后的萧条时期,食物实行配给制,当Helene Hanff在通信中得知了这一情况后,她买了各种食物从伦敦源源不断寄往英国,有火腿、鸡蛋、巧克力以及时髦的女士丝袜等。海莲为这些从未见过面的人付出的慷慨与善良使得书店里的人倍感温暖,Helene与全书店的人成为朋友,Helene生日的时候还收到了来自书店的一本三边的页缘都上金的书——《伊丽莎白时期情诗选》,她在回信中无不感激表达了欢喜:“你们知道吗?我竟在生日当天收到这本书!”
这一封封飞跃大西洋的书信,聊的不仅仅是关于购书,他们会聊各自的生活,家人的照片,还分享彼此喜欢的球队,谈论书籍的翻译、装帧,海莲还谈论自己的编剧工作,书店里的女店员也调皮地悄悄写信给Helene描述Frank。同时,Frank的妻女也写信给Helene,书店员工还邀请Helene到伦敦游玩,并且提供食宿。只可惜,直到Frankie去世,海莲也没有机会前往伦敦。
Helene Hanff一生潦倒穷困,一直居住在纽约,不同于同时期的作家E.B.怀特那样走运,收获声名与财富,坐拥不菲的版税收入。相反,海莲可以说是在纽约住了半辈子却一直饱受穷困,她略乏才气却嗜读好书,她嫌纽约这个城市没有气质,买不到她想读的书,在电影版《查令十字街84号》里,饰演海莲·汉芙的女演员Anna Maria Louise ltaliano一上场就开骂了:“全纽约市没人读英国文学啦?”她只好转而向伦敦的一家小旧书店邮购那些“这年头没人要买的英国佬写的英文书”(电影一开始,被汉芙索书不成的美国某书店经理的话)。于是,一桩原本单纯的买卖关系竟成就了长达二十年、多人参与的越洋友谊。
《查令十字街84号》的译者陈建铭先生在《关乎书写,更关乎距离》一文中写道:我始终相信,把手写的信件装入信封,填了地址、贴上邮票,旷日费时投递的书信具有无可磨灭的魔力——对寄件人、收信者双方皆然。其中的奥义便在于“距离”——或者该说是“等待”——等待对方的信件寄达;也等待自己的信件送达对方手中。这来往之间因延迟所造成的时间差,大抵只有天然酵母的发菌时间之微妙差可比拟。
随性的美国大龄女作家,内敛的英国旧书店老板,以书为名的志趣相同,延绵出二十年未曾谋面的邮件交流。远隔重洋的字里行间,优雅缓慢含蓄谦逊,工作生活无所不谈,你来我往之间,牵动了心灵的相惜,渗透了人情的温暖,穿插了那个遥远年代纽约伦敦的社会政治变迁。书信的往来代表了一份期盼,等待的过程会将情感延长,柏拉图式的默契神交,赋予了两段并无关联的人生温润的精神陪伴。
由Anna Maria Louise ltaliano与Philip Anthony Hopkins主演的同名电影《84 charing cross road》于1987年在美国上映。影片中结尾Helene Hanff坐在家中的地毯上,身后的窗外是纽约阴沉的天空,她蓬松的卷发已经开始泛白,手中拿着一本书小心翼翼地擦拭,眼前全是书,此时画外音响起:
“亲爱的Kay和Brian,我抽出时间清理书架,坐在地毯上,身边都是书,祝你们一路顺风,希望你们在伦敦玩得愉快,或许我没有到过那边也好,我期盼了好多年,过去我常看英国电影,只为了瞧瞧那些街道。多年前,有朋友说:‘到英国去的人,都能找到他们想找的东西,我说我想去找英国文学中的英国,他点头说,他就在那里’,也许在,也许不在。环顾四周,我确定一件事,他就在这里”。
此时她颤抖的起身走到窗边的桌子旁,拿起一支香烟点燃,背靠着窗边,脸上是迟暮之年的悲戚与伤感,画外音继续:
“卖书给我的人几个月前去世了,书店老板马克先生也去世了,但马克书店还在那里,虽然听说他会被拆除,但求求老天不要。如果你们刚好经过查令十字街84号,请替我献上一吻,我亏欠他良多。”
其实,在原著中故事到这里已经结束,这段写于1969年4月11日的信,是Helene Hanff写给友人凯瑟琳的:其中电影中删除的一段话是:“我希望你和布莱恩在伦敦能玩得尽兴。布莱恩在电话里对我说:“如果你手头宽裕些就好了,这样子你就可以跟我们一道去了。”我一听他这么说,眼泪差点儿要夺眶而出。大概因为我长久以来就渴望能踏上那片土地……我曾经只为了瞧伦敦的街景而看了许多英国电影......”Helene这个大半生居住在伦敦的寂寂无名的作家,生前一直经济拮据,长达20年的时间里,她几次想前往伦敦,都因各种事情而最终未能如愿踏上伦敦。而在电影里面,稍显温情,为这段书中未竟的故事补上了一个结尾:
Helene望向窗外的纽约,良久,她冲向卧室,拿出行李箱,翻出电话本,打电话给书店,卖掉了自己的一本《伦敦旅游指南》,而紧接着画面调转,Helene Hanff已经站在伦敦的查令十字街84号上的马克斯与科恩书店内,她久久矗立,眼中蓄着泪水,良久,说出那句“here i am,frankie,i finally made it”。

一样产自英国的了不起小说家格林,在他的《哈瓦那特派员》中说:“人口研究报告可以印出各种统计数值、计算城市人口,借以描绘一个城市,但对城里的每个人而言,一个城市不过是几条巷道、几间房子和几个人的组合。没有了这些,一个城市如同陨落,只剩下悲凉的记忆。”——是的,1969年之后,对Helene Hanff来说,这家书店、这道书街已不可能再一样了,如同陨落,只因为“卖这些好书给我的好心人已在数月前去世了,书店老板马克斯先生已不在人间”,这本《查令十字街84号》于是便成为一本哀悼伤逝的书,纪念美好善良的人心在二十年书籍时光中的一场奇遇。把这一场奇遇写成书,这一切便不容易再失去一次了,甚至自此比她自身的生命有了更坚强抵御时间冲刷的力量——人类发明了文字,懂得写成并印刷成书籍,我们便不再徒然无策地只受时间的摆弄宰制,我们甚至可以局部地、甚富意义地击败时间。书籍,确实是人类所成功拥有最好的记忆存留形式,记忆从此可置放于我们的身体之外,不随我们的肉身朽坏。也因此,那家书店,当然更重要是用一本一本书铺起来的查令十字街便不会因这场人的奇遇戛然中止而跟着消失,事实上,它还会因多纳入Helene Hanff的美好记忆而更添一分光晕色泽,就像它从不间断纳入所有思维者、纪念者、张望者、梦想者的书写一般,所以哀伤的Helene仍能鼓起余勇地说:“但是,书店还在那儿,你们若恰好路经查令十字街84号,请代我献上一吻,我亏欠她良多……”
今天,即便84号的“马克斯与科恩书店”很遗憾如书末注释说的,没再撑下去,而成为“柯芬园唱片行”,但查令十字街的确还好好在那里,周围满是酒吧和书店,麦当劳的店址赫然矗立,人们乘兴而来,也未必败兴而归,84号还是84号,书店却在人们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