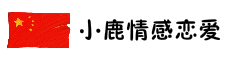Take them like they're ours,
We're guilty of that crime
Oh, that's just how the story goes
大约七岁以后,我开始有了一些对连环画以外的图书的记忆,妈妈的朋友们邻居们诸多在出版社,年复一年的,我逐渐就有了一柜子一柜子的书做朋友。
但所谓世界文学名著之类的,在小的时候还是先以某个出版社的图解版出现在我面前的。比如但丁的《神曲》,至今我也没读过全文,印象还停留在小时候看的那些图上。
说到阅读文字带来的震撼,目前还有印象的,是小学读《绝代双骄》和《倚天屠龙记》,以及初中读《牛虻》。牛虻被处决留下的那封信,让我平生第一次对着一本小说嚎啕大哭,哭得撕心裂肺、肝肠寸断。之后再有印象读书哭成这样的,就是三十岁左右看《我的团长我的团》龙文章自杀那段了。

我的记性很差,所以大学每周去图书馆抱一批书回来,读了什么,真的不是很确定。有印象的都是一些《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后现代精神》之类的。但所谓名著,应该也并没少看。
但于我至今都会反反复复想起来,反反复复再买,反反复复再看的,一共就三本书,《呼啸山庄》《**时期的爱情》和《麦田里的守望者》。我猜它们于我,一定有某种特别的意义。
这几天我本来在家闭关,第一个三天闭关结束后,深感质量不到位,于是调整了一天,决定再闭关七天。然而今天才是这七天的第二天,一早从睡过了错过了上午的两座打坐开始,闭关就已经失败了。中午又因为收快递打破了止语的规矩,到了下午,还是没能驱动成功自己追回这一天的四座修行,我已经变得有些沮丧。
躁郁海浪又一次交替换防。今天的我变得完全不似昨天的我。但如果就这样失去对这一天的主控权,着实不甘心,于是冒着小雪取回来的双语版《呼啸山庄》和中文版《**时期的爱情》成了我今天的主食。
看了《呼啸山庄》英文版开篇第一段落,查单词查到手抽筋。于是就明白了自己为什么喜欢它。你就看看前几行这些单词吧:solitary(孤独的)、misanthropist(厌世者)、desolation(荒凉)、suspicioursly(可疑的)、no sympathizing(毫无同情的)、exaggeratedly reserved(极度冷淡)。真是每一粒都算天蝎座每日必服之良药。
我之所以查单词,而不是去依靠中文版翻译,是真的想弄清楚原著表达了什么。但当这一串谜一样冷淡的单词加上“to express the hope that I have not inconvenienced you by my perseverance in soliciting the occupation of Thrushcross Grange…”这样的长句砸在一起的时候,我真觉得念起来气不够。
我必须得说,以我粗鄙的英文基础,我读完第一段,心中生成的句子,跟目前我看到的中文版(孙致礼先生翻译译林出版),翻译的一点都不一样。
“等我通报姓名时,他把手指更深地藏进背心口袋里,显出一副绝不掉以轻心的神气。这当儿,他全然没有想到,我心里对他萌生了几分好感。”
“他一点都想象不到,虽然我注视他时,他的黑眼睛在眉毛下闪烁着怀疑,我已经走上前去,他的手指还孤傲的抵抗着更深的藏进衣服,但我已经被他所吸引。”
如果每段话我心里生成的句子都跟翻译版不同,那当我们读译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读THE BOOK,THE STORY呢?
于是我暂时放弃了一路查字典的企图,拿起了杨玲先生译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看到医生之死,男主出场,惨遭女主时隔半个世纪再次拒绝,已经画了满书的道子,觉得每句话都太妙了。
比如:医生看着刚因为恐惧老去而自杀的好友拍的那些照片想——
“有很多次他都心痛的想,在这个由一张张不经意间拍下的照片组成的画廊里,就孕育着这座城市的未来:它得由那些性格不定的孩子们统治,并最终被他们毁灭,连一丝昔日荣耀的灰烬也不复存在。”
形容一个人的精确与严谨——
“像编制绳索般严谨地还清了最后一分钱。”
提及下棋——
“与其说是一门学问,不如说是一种理性的对话。”
“她们的爱情迟缓而艰难,常常被不祥的预兆干扰,生命对她们来说简直没完没了” 。
“一大群嗜血的蚊子从沼泽中飞起,带着一股柔柔的人粪气味,温热而感伤,扰得灵魂深处泛起对死亡的坚信”。
“但面对毫不让步的死神,她只得投降。她的痛苦化作一股对世界、甚至对自己的盲目怒火,而这反而给她注入了自控的力量和独自面对孤独的勇气。”“当被人爱着的人死去时,真该带上他所有的东西。”
这些句子,无论看着还是念着、想着,都简直要爱上写作者(或者说作家和翻译家两个人)。
我跟好友分享这些句子,好友吐槽说,“作家就是作家,比你厉害太多了”。我忍不住爆出了脏口,“拿我跟马尔克斯比,你真抬举我,朋友。你就不能拿我跟……”于是很悲惨的一时没想出来哪位我真的认为是作家的作家比我差……勉强心虚的硬敲出“韩寒”两个字。
最近和包大师听了很多音乐,也聊了很多音乐,也聊到了这些音乐背后的时代信息。在这个过程中,我突然恍然大悟的惊呼,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现在不喜欢《恋爱的犀牛》了。
大学小剧场话剧看足了,什么实验话剧都没落下过。学生票大概二三十块,我和同宿舍的伙伴经常骑着自行车从东五环外骑到人艺小剧场。第一次看《恋爱的犀牛》还是1999年,感受是超级震撼的,特别是男主这段独白——
“我爱你,我真心爱你,我疯狂地爱你,我向你献媚,我向你许诺,我海誓山盟,我能怎么办。我怎样才能让你明白我是如何的爱你?我默默忍受,饮泣而眠?我高声喊叫,声嘶力竭?我对着镜子痛骂自己?我冲进你的办公室把你推倒在地?我上大学,我读博士,当一个作家?我为你自暴自弃,从此被人怜悯?我走入神经病院,我爱你爱崩溃了?爱疯了?还是我在你窗下自杀?明明,告诉我该怎么办?”
彼时,我觉得我完全明白,甚至感到窒息和恐惧。
又过了十年,我又看了一遍《恋爱的犀牛》,对他们的纠缠感到困惑。何必呢?
再过了十年,我再想起《恋爱的犀牛》,已经没有任何想再看一遍的欲望了。
是因为我老了么?
不只是。
1999年,还是一个相信爱情且要去证明爱情的时代,2009年,是一个怀疑爱情,也不再用物质以外的方式证明爱情的时代,而2019年,在这个时代,你甚至不好意思让人知道你还会思考关于“爱情”这么俗套的命题。
十年前,我们会因为有人背叛一段感情而义愤填膺,而现在,我们会不好意思跟人提起自己还会为背叛这种事情纠结。时代会慢慢驯化你。而时代,除了科学技术逻辑之外,还有一部分,其实就是身处其中的人心的总和。到底是时代让我们变得冷漠,还是我们的冷漠改变了时代的底色?
但老了还是有老了的好处,比如,现在的我,不会再觉得爱情的无常是源自哪一方不够努力或者抢先离场。我会明白,心同此心,所以对爱情的逐渐无感,就像我们会对买回家的一件衣服、一样电器逐渐无感一样,是无可避免的。维持“我会永远爱你”的誓言不成为谎言,需要的力气比我们想象中要大太多了。就像你要求一件衣服每天都自动换颜色换款式换材质那么困难。
这一题,不是解题方法不对,而是题不对。
但说着如此茕茕孑立的话,我还是忍不住问了自己两个问题:
第一,我们能以菩提心和世俗心同时来爱世人吗?
第二,如果我们已经有了菩提心的爱,还会需要世俗心的爱吗?
还会吗?
“费尔明娜,”他对她说,“这个机会我已经等了半个多世纪,就是为了能再一次向您重申我对您永恒的忠诚和不渝的爱情。”
——《**时期的爱情》
死啦死啦:“师座说我是短兵相接的天才,百战百败的天才,偷鸡摸狗的天才,那都是虚的。我现在说实的。”他忽然笑了一下,又悲伤又骄傲,那股吹破天的劲又上了脸,本来从南天门上下来后它已踪影不见:“实地就是,我只想让事情是它本来该有的样子——我是这么一个狗屁不通的天才!条条路都走不通,可我还是做不到,做不到你们要我做的,把陋习说成美德,把假话变成了规矩,把抹杀良心说成明智,把自私说成了爱国,把无耻变成了表演,把阳痿说成守身如玉,把欺凌弱小说成正义,把人变成炮灰,把炮灰变成荣誉……”“师座,西进吧!别北上”。
明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就要被枪毙了,因此我如果真要履行诺言告诉你一切,现在就必须履行了。
我的心愿就是要你明白,为什么我一直像一头发怒的野兽那样对待你,为什么迟迟不肯把旧怨一笔勾销。当然,你知道个中原委,我所以要告诉你,只不过是写这些字能给我以乐趣而已。我是爱你的,琼玛,当你还是一个难看的小姑娘,穿一件花格子罩衫,围一个皱巴巴的胸褡,背拖一条小辫子的时候,我就已经爱上了你;我现在还爱着你。你还记得有一天我吻了你的手,而你那样可怜巴巴地央求我‘请你以后不要这样’那件事吗?我知道那是一种不光彩的把戏;但你必须原谅我。现在,我又吻了这张纸上写你名字的地方。这样,我就吻过你两次,而两次都没得到你的允许。
就说这些了。别了,亲爱的。
无论我活着
还是失去生命
都将是一只
快乐的牛虻
——《牛虻》
如果你的生命注定无法停止追逐
我也只能为你祝福
——《你走你的路》
我们其实永远无法戒掉经验或者说他人对我们的影响。出现在我们世界里的一切文本、一切声音、一切景象、一切图像……的叠加,都让我们以为自己的选择是“自己的”。
就单说此世的这个所谓的“我”前半生的爱情观,小时候听张雨生,觉得爱情要像《天天想你》一样高尚且凛冽,又觉得结局必然如《你走你的路》一样注定孤独,觉得《牛虻》的暗恋与临死才说,才是正确的表达方式,觉得《**时期的爱情》的等你就等半个世纪,才算坚定不移。
如果拆解开,哪一个,其实都不是“自己的”,但这些他人的创造叠加在一起,就像重组的DNA一样,调制出了一杯关于爱情的特饮。它们和原生家庭特质差不多的影响着我的感情基因。让我与男主角们的相遇和互动,必然会呈现以上行为特质和态度特质。
但如今我再看这个前半生,并不觉得充斥着辜负与被辜负。它们像路标一样引导我走到某一个临界点上,忽然明白,当你能超越爱本身,爱就永恒了。不要执着于当时当下的不离不弃,生命就是因为恒常的无常才可以流动。
第一,我们能以菩提心和世俗心同时来爱世人。
第二,如果真的生起了菩提心,就渐渐没有什么菩提心与世俗心的分别,就算做世间事,也依然可以用菩提心。世俗心的爱也就不是以前理解的世俗心的爱了。
那么,在生起菩提心之前,我们应该怎样去爱,或者面对怎样的爱?
我暂时还没思考过问题三。我只能先敷衍的说,王千源在《大人物》里的背肌真好看,隔着衣服都能看到肌肉的线条的美感,瘟疫公司hard模式关闭后,我真的要开始撸铁了。
马尔克斯在《**》的开头,用了50页的篇幅写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其实这都间接描绘了人到古稀的女主是怎样的一个人。我用了四千字记录了一个闭关失败的冬日,其实都间接的扫描了我的脑洞。